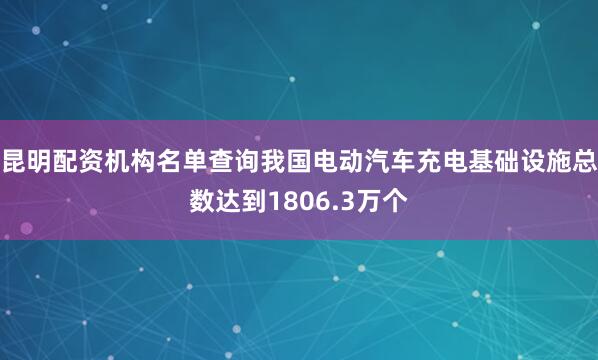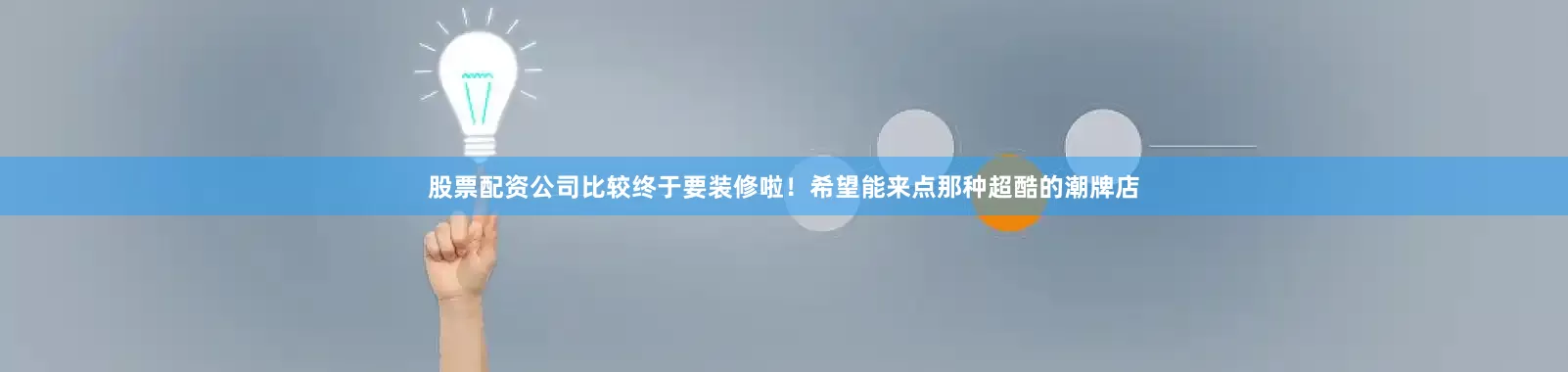“创作声明:本故事纯属虚构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。图片和文字均不涉及真实,人物名称皆为化名。”
“听着,别犯傻,让你的狗离咱们自己的坦克远点!”一个老兵猛地拽住身边年轻的训犬员,压低了声音吼道。
训犬员愣住了,满脸困惑地看着他:“你说什么胡话?它们的目标是德国人的铁皮罐头!”
“目标?”
“你告诉我,过去三个月,它们是在哪种坦克的肚子底下找到食物的?是闻着德国佬那股刺鼻的汽油味,还是我们自己这该死的柴油味?”
训犬员的脸瞬间血色尽失。他眼睁睁看着第一条军犬被放出战壕,它兴奋地摇着尾巴,在震耳欲聋的战场上,用它训练有素的鼻子,努力分辨着空气中那股与食物画上等号的、熟悉的气味。
它绕过了一辆近在咫尺的德军坦克,仿佛那东西根本不存在。然后,它加速了,笔直地冲向了另一侧……

1
1941年的秋天,烂泥和绝望一样深。德军的钢铁履带碾碎了防线,也碾碎了无数血肉之躯。
伊万趴在冰冷的堑壕里,泥水浸透了他的棉衣,让他感觉自己像一块正在腐烂的木头。他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,那里有无尽的森林和真正的冬天,而不是眼前这种黏糊糊、半死不活的季节。
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炸开,震得泥土簌簌落下,糊了他一脸。他抹了把脸,手心蹭到的不是泥,是某种温热黏腻的液体,他甚至懒得去分辨那属于谁。
“喂,伊万,还有‘莫洛托夫鸡尾酒’吗?”旁边一个叫谢尔盖的列兵哑着嗓子问,他的半边脸被熏得漆黑。
伊万摇了摇头,把手里空了的伏特加瓶子扔到一边。“最后一个刚才喂了那辆三号坦克,连层漆都没给它蹭掉。”
谢尔盖苦笑了一下,牙齿在昏暗中显得格外白。“我们的反坦克枪,打在它们身上就跟挠痒痒一样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,“我亲眼看见,一整排的兄弟,就那么被压过去了,像压过一堆麦子。”
伊万的心脏猛地抽紧了。他不想去想那个画面,但那声音,骨头碎裂和金属碾压的混合声,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。他是个训犬员,不是坦克猎手。他的手更习惯于抚摸狗的皮毛,而不是扣动扳机。
战争把一切都扭曲了。他带来的那几条信鸽,在第一次尝试穿越火线时就被机枪打成了血雾。现在,他身边只剩下“闪电”,一条聪明、强壮的东欧牧羊犬。
几天后,连队指导员把他们这些还活着的、跟动物打过交道的人都召集了起来。指导员的脸色和天气一样阴沉,他手里捏着一份电报,纸张边缘都有些潮了。
“最高统帅部下达了紧急命令。”指导员的声音很干涩,“鉴于前线反坦克武器严重短缺,决定启动一项‘特殊武器’计划。”
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,脸上带着一丝病态的期待。也许是某种新式火箭筒,或者威力巨大的地雷。
指导员清了清嗓子,眼神扫过每一个人,最后落在了伊万身上。“命令要求,征调所有军犬,特别是中大型犬,用于组建‘反坦克犬连’。”
空气死一般的寂静。伊万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快凝固了。他看着指导员,试图从对方的脸上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,但他只看到了不容置疑的严肃。
“用狗……去炸坦克?”谢尔盖难以置信地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。
“是的。”指导员的回答斩钉截铁,“这是命令。伊万同志,你是我们这里最有经验的训犬员,你和你的狗‘闪电’,将成为第一批学员。”
伊万张了张嘴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能感觉到“闪电”似乎察觉到了他情绪的变化,正用头轻轻蹭着他的腿。那温热的触感,此刻却像烙铁一样烫人。他低下头,看着“闪"电”那双清澈、充满信任的眼睛,一阵恶心从胃里翻涌上来。
2。"科学"两个字从项目负责人波波夫教授嘴里说出来时,带着一股实验室的冰冷味道。他是个戴着厚厚眼镜的学者,说话时习惯性地挥舞着手臂,仿佛在指挥一场交响乐。
“同志们,原理很简单!这是伟大的巴甫洛夫同志的条件反射理论的完美应用!”波波夫站在一辆静止的T-34坦克旁边,情绪高昂地宣布,“我们让狗保持饥饿,然后把食物放在坦克底下。经过反复训练,狗的大脑里就会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连接:坦克底盘等于食物!”
训练场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片空地上。几十条狗被关在笼子里,饥饿的呜咽声此起彼伏。伊万的“闪电”也在其中,它焦躁地在笼子里打转,不时用鼻子拱着笼门,望着伊万,眼神里满是困惑。
“记住,必须让它们饿透了!”一名军官严厉地对伊万说,“只有饥饿,才是最好的驱动力。”
伊万点了点头,心脏却像被一只手攥住了。每天,他都必须亲手将那份少得可怜的、混着锯末的食物,放到冰冷的T-34坦克车底。然后,他会打开笼子,“闪电”会像一道黑色的影子一样冲出来,毫不犹豫地钻进车底,狼吞虎咽地吃掉那点食物。
每当这时,伊万都会别过脸去。他能感觉到“闪电”吃完后跑回他身边,用头蹭他时,皮毛下微微颤抖的身体。那不是兴奋,是恐惧。坦克的巨大阴影,柴油发动机那股刺鼻的气味,还有偶尔发动的轰鸣声,都让“闪电”感到不安。
伊万试过在夜里偷偷给“闪电”加餐。他把自己的黑面包省下来,捏碎了塞给它。但第二天,军官检查了狗的粪便,立刻发现了问题。
“伊万同志!你的同情心是在谋杀你的战友!”军官的吼声在空旷的训练场上回荡,“战场上,它犹豫一秒,可能就是一辆坦克冲进我们的阵地!你是在犯罪!”
伊万被罚禁闭二十四小时。在黑暗潮湿的禁闭室里,他能清晰地听到外面“闪电”不安的刨地声和低吠声。那一刻,他恨的不是那个军官,而是他自己。
有一次,一个来自工程兵部队的老兵忍不住提出了疑问。“波波夫教授,我们训练用的是T-34,烧的是柴油。可德国人的坦克,大部分烧的是汽油。气味完全不一样,狗能分得清吗?”
波波夫教授推了推眼镜,不耐烦地回答:“理论上,狗是根据坦克的形状和声音来定位的,气味只是辅助。再说,我们现在哪有时间去弄一辆能开的德国坦克?时间紧迫,同志们,前线等不了!”
老兵还想说什么,但被旁边的政委一个眼神制止了。质疑“科学”,就是质疑命令。
伊万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,心里的不安像野草一样疯长。他发现,“闪电”在训练中越来越依赖嗅觉。它会先在空气中嗅闻,确定了那股熟悉的柴油味后,才会冲过去。对于坦克的轰鸣,它始终无法完全适应,每次引擎发动,它的耳朵都会紧张地贴在脑后。
伊万和“闪电”之间的默契,变成了一种无声的折磨。他抚摸它的背,能清晰地感觉到它每一块紧绷的肌肉。他看着它的眼睛,那里面不再是纯粹的信任,而多了一丝被饥饿和恐惧折磨出的神经质。
他开始在训练的间隙,用身体挡住别人的视线,悄悄地把手伸到坦克底下,让“闪电”舔舐自己手心的汗水,而不是去碰那冰冷的金属。他想用自己的体温,去抵消那钢铁的冰冷。
“你是个好孩子,闪电。”他会用只有他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说,“你只是……只是在玩一个游戏,对吗?一个找食物的游戏。”
“闪电”会呜咽一声,把头埋进他的怀里。它不知道什么是战争,什么是武器,它只知道,那个它最信任的人,正在让它去做一件它非常、非常害怕的事情。
3
"反坦克犬连"这个番号听起来既滑稽又悲壮。当他们乘坐闷罐车开赴莫斯科前线时,没有人笑得出来。
车厢里挤满了人和狗,空气中混合着汗味、狗身上的味道和廉价烟草的呛人气味。伊万紧紧地抱着“闪电”,把自己的大衣分了一半给它盖上。火车铁轨发出单调的“咯噔”声,像是在为他们倒数生命。
“闪电”很安静,它把头枕在伊万的腿上,似乎睡着了。但伊万能感觉到它身体的轻微颤抖。他知道它没睡,它只是在假装。就像他自己一样,假装平静,假装自己是个坚强的战士,而不是一个即将把伙伴送上死路的刽子手。
车厢的角落里,谢尔盖正低着头,用一把小刀削着一小块木头。他的狗,一条叫“黑星”的杂种犬,安静地趴在他脚边。
“嘿,伊万。”谢尔盖没抬头,声音很低,“你说,它们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吗?”
伊万抚摸着“闪电”的耳朵,那里的软毛像天鹅绒一样光滑。他沉默了很久,才说:“不知道。对它们来说,可能只是最后一次找食物。”
“我倒希望它知道。”谢尔盖突然说,手里的刀停了下来,“我希望它知道,它是为了保卫莫斯科。这样,它也算是个英雄。”
伊万没有接话。英雄?把炸药绑在一条饿坏了的狗身上,让它冲向坦克,这是英雄主义,还是人类的无耻?他不知道答案。
临战的前一夜,他们被部署在莫斯科城外的一处残破阵地上。德军的炮火准备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,整个大地都在颤抖。天空被照明弹和炮火映成一片诡异的橘红色。
伊万从自己的口粮袋里,拿出了全部的存货:一块黑面包,还有一小节风干的香肠。这是他准备留着应急的,但他现在顾不上了。
他把“闪电”拉到一处弹坑的角落,避开所有人的视线。他把面包和香肠一点点撕碎,喂到“闪电”嘴里。

“吃吧,孩子,多吃点。”他的声音在炮火的间隙中显得格外沙哑,“吃饱了,跑得快。”
“闪电”大口地吞咽着,这是它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餐。它吃完后,不停地舔着伊万的手,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咕噜声。伊万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。他紧紧地抱住“闪电”,把脸埋在它温暖的颈毛里。那熟悉的、让他安心的气息,很快就要永远消失了。
“听着,闪电。”他贴着它的耳朵说,“明天,如果……如果情况不对,你就跑,知道吗?别管什么坦克,别管什么食物,往回跑,跑到林子里去,藏起来。你那么聪明,一定能活下去的。”
“闪电”似乎听懂了,又似乎没懂。它只是安静地任由伊万抱着,尾巴轻轻地扫着地面。
天亮了。德军的坦克像一群灰黑色的甲虫,从地平线上涌了出来。坦克的轰鸣声由远及近,地面震动得越来越厉害。
“‘狗弹’部队!准备出击!”指挥官的嘶吼声在战壕里响起,带着一丝疯狂的决绝。
伊万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。他和其他训犬员一起,机械地从箱子里取出那些特制的帆布背心。每一件背心里都塞着几公斤的烈性炸药,背上竖着一根木质的触发杆,大约二十厘米高。只有当狗钻到足够低矮的坦克底盘下,这根触发杆被向下压动,才会引爆炸药。
他的手抖得厉害,几乎扣不上背心上的皮带扣。他能感觉到“闪电”身体的僵硬,它不安地扭动着,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。
“别怕,别怕……就是一件新衣服。”伊万的声音也在发抖,他不知道是在安慰狗,还是在安慰自己。
他最后一次检查了背心,然后深吸了一口气,拔掉了触发杆上的保险销。这个小小的金属栓,此刻在他手里重如千斤。
“伊万!你还在磨蹭什么!”政委在他身后怒吼。
伊万没有回头。他蹲下身,与“闪电”平视。他看到了那双他无比熟悉的眼睛,里面充满了信任,也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“游戏”的困惑。它不知道这件“新衣服”意味着什么,它只知道,前面有坦克的轰鸣,有熟悉的柴油味,也许,还有食物。
伊万伸出手,最后一次重重地拍了拍“闪电”的后背。
“去吧!”他用尽全身力气喊道。
“闪电”像一支离弦的箭,猛地窜出了战壕,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战场上弥漫的硝烟之中。
不远处,一个叫卡佳的卫生员正紧张地注视着这边。她刚刚给一个被弹片划伤的士兵包扎好伤口,目光就和伊万对上了。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
“伊万,你……”她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。
伊万只是对她扯动了一下嘴角,那比哭还难看。他转过头,死死地盯着“闪电”消失的方向。
卡佳看着他紧绷的侧脸和微微颤抖的肩膀,心里一紧。她低声说:“你一定要回来,伊万。仗打完了,我请你喝真正的茶,不是用桦树叶煮的那种。”
伊万的身体僵了一下,没有回头,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他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了战场上,那个小小的、正在奔跑的黑点上。

卡佳咬着嘴唇,她知道,这种时候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。她只是觉得,如果这个男人能活下来,她想再看到他抚摸那条狗时,脸上露出的那种温柔的表情。
“回来了一定要来找我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几乎被炮火声淹没,“我……我等你。”
伊万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。他想回头对她说些什么,但就在这时,战场上的景象让他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——
4
“闪电”冲出战壕后,立刻就懵了。
训练场上从来没有过这样震耳欲聋的炮声,没有子弹贴着头皮呼啸而过的声音,更没有这么多移动的、喷吐着火舌的钢铁怪物。它本能地停下脚步,茫然地在原地转了一圈,尾巴也惊恐地夹了起来。
战场上不止它一条狗。几十个黑点在硝烟中乱窜,像没头的苍蝇。有的狗刚跑出去没多远,就被德军的机枪扫倒,发出一声短促的悲鸣。有的被巨大的爆炸声吓破了胆,掉头就往回跑,冲向自己的战壕。
“回来!回来!你这该死的畜生!”一名训犬员惊恐地尖叫着,试图拦住自己那条往回跑的狗,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一声巨响,那条狗在战壕边缘爆炸,泥土和血肉溅了所有人一身。
伊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他跪在战壕的边缘,不顾随时可能飞来的流弹,死死地盯着“闪电”。“跑啊,闪电!往林子里跑!快跑!”他在心里疯狂地呐喊,但声音却卡在喉咙里,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
就在这片混乱中,“闪电”似乎终于找到了方向。它那训练有素的鼻子,在混杂着火药和血腥味的空气里,捕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。
是柴油味。
那是它在训练场上闻了无数遍的、与食物紧密相连的气味。那个味道,就是命令,就是目标!
它的犹疑瞬间消失了。它重新迈开四肢,像过去几百次训练中一样,朝着那股熟悉的味道狂奔而去。
伊万的瞳孔猛地收缩了。他眼睁睁地看着“闪电”绕过了一辆正在开火的、散发着汽油味的德军四号坦克,然后,毫不犹豫地、满心欢喜地,冲向了不远处一辆正在为步兵提供火力掩护的苏军T-34坦克!
“不——!”
伊万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,他想站起来,想冲出去,但他被身边的谢尔盖死死地按住了。
“来不及了!伊万!来不及了!”谢尔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在伊万血红的视野里,“闪电”轻巧地一矮身,熟练地钻进了那辆T-34坦克的车底。对于它来说,这是游戏结束、得到奖励的信号。
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长了。伊万甚至能想象出“闪电”钻进去后,发现底下没有食物时的那一瞬间的困惑。
然后,一声沉闷而巨大的爆炸声响起。
那辆T-34坦克庞大的身躯猛地一震,左侧的履带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撕扯开来,断裂的金属节飞向半空。坦克歪斜着停了下来,一股黑烟从车底滚滚冒出,车上的机枪瞬间哑火。
伊万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他什么也听不见了,只看见那团黑烟,那团吞噬了他的“闪电”、也吞噬了他所有希望的黑烟。
几乎在同一时间,苏军阵地的其他几个方向,也接二连三地响起了同样的爆炸声。
“我的坦克!我的坦克!是我们的狗!”一名坦克车长从炮塔里探出半个身子,歇斯底里地吼叫着。
“射击!向那些狗射击!别让它们靠近!”一名苏军军官反应了过来,发出了一个无比荒诞的命令。
战壕里乱成一团。苏军士兵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他们曾经抚摸过、喂食过的军犬,此刻正兴高采烈地冲向自己的坦克,然后变成一团团致命的火焰。
对面的德军阵地上,起初也是一片寂静。德国人显然被这诡异的景象搞懵了。他们看到一群狗冲出苏军战壕,但奇怪的是,这些狗对他们的坦克视而不见,反而径直冲向了苏军自己的坦克阵地。
当第一辆T-34被炸毁时,一名德军坦克指挥官从观察镜里看到了全过程。他愣了几秒钟,然后拿起无线电,用一种难以置信的、夹杂着狂喜的语气喊道:“他们……他们在用狗炸自己的坦克!上帝啊,俄国人疯了!”
很快,德军阵地上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。那笑声穿过炮火的喧嚣,清晰地传到了苏军的阵地里,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,抽在每个苏军士兵的脸上。有的德国兵甚至停止了射击,饶有兴致地趴在坦克上,像看马戏一样,指着那些在战场上乱窜的“自杀式”军犬。5
战斗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结束了。德军并没有趁势发起总攻,他们似乎被这场闹剧的娱乐效果冲淡了进攻的欲望。
战后的清点工作,像一场漫长的葬礼。这次“反坦克犬”的首秀,战果是摧毁德军坦克数量为零。而苏军这边,三辆T-34被炸断履带,彻底瘫痪在阵地前,另有两辆轻型坦克受损。更不用提那些被自己人射杀,或者在混乱中引爆,造成己方步兵伤亡的“狗弹”。
伊万像个行尸走肉一样,被人从战壕里拖了出来。他的脸上、身上全是泥土和黑灰,眼神空洞得吓人。他没有受伤,但感觉自己身体里的什么东西,已经跟着那声爆炸一起碎掉了。
他被带到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接受审查。那个曾经唾沫横飞的政委,此刻脸色灰败,像一只斗败的公鸡。项目负责人波波夫教授则不停地用一块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,嘴里反复念叨着:“这不科学……这不符合逻辑……”
“伊万同志,你必须解释清楚!”一名来自内务部的官员用冰冷的目光盯着伊万,“为什么你的狗,会攻击我们的坦克?这是训练的失误,还是……故意的破坏?”
伊万缓缓地抬起头,空洞的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丝焦点。他看着那名官员,又看了看旁边的波波夫教授,嘴角扯出一个嘲讽的弧度。
“为什么?”他沙哑地重复了一遍,声音不大,却让整个帐篷里的人都打了个寒噤,“您应该去问教授。问他为什么我们的狗,闻了几个月的柴油味,却要让它们在战场上自己去找汽油味!”
波波夫教授的脸瞬间涨红了:“我解释过!理论上,视觉和听觉才是主导!是战场环境太复杂,干扰了它们的判断!”
“是吗?”伊万冷笑一声,“我只知道,一条饿坏了的狗,会不顾一切地扑向它熟悉的、代表食物的味道。这是本能,不是理论!”
“你这是在推卸责任!”政委找到了攻击点,立刻跳了起来,“你是训犬员!你没有控制好你的狗!”
“控制?”伊万站了起来,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,“我怎么控制?在它冲出去的那一刻,我就已经失去了控制!是你们,把它从我的伙伴,变成了一颗连目标都分不清的炸弹!现在炸到了自己,你们却来问我为什么?”
帐篷里一片死寂。没有人能反驳他的话,因为战场上的结果,就是最残酷的证据。
审查最终不了了之。责任太大了,没有人能承担。最终,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被送了上去,将失败归咎于“德军狡猾的战术干扰和战场复杂电磁环境”。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心知肚明,这不过是自欺欺人。
伊万被暂时解除了职务。他在后方的营地里游荡,像一个幽灵。他看到卡佳,那个曾对他说“我等你”的卫生员,远远地向他走来。
卡佳的脚步有些犹豫,她走到伊万面前,张了张嘴,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最后,她只是低声问:“你……还好吗?”
伊万看着她,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。“我看见了。”他说,“德国人……他们在笑。”
卡佳的心一沉。她知道,对于一个士兵来说,这比死亡更难以承受。
“那不是你的错,伊万。”她轻声说。
“是吗?”伊万的目光越过她,望向远方,“我亲手给它绑上了炸药。我亲口对它下达了‘去’的命令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它冲向了我们的坦克。如果这不是我的错,那是谁的错?”
他没有等卡佳回答,转身默默地走开了。他的背影,在冬日的斜阳下,被拉得很长,很孤独。
6
“反坦克犬”计划并没有因为第一次的灾难性失败而立刻终止。在巨大的战争压力下,任何一丝可能获胜的希望,都会被紧紧抓住,哪怕这希望荒诞不经。
苏军高层进行了艰难的“调整”。他们费了很大力气,从后方运来几辆缴获的、还能开动的德军坦克,专门用于训练。训练场上开始播放机枪射击和炮火轰鸣的录音,试图让狗提前适应战场环境。
伊万也被重新召回了队伍。他被分配了一条新的狗,一条看起来很凶悍的高加索犬。但他再也找不回以前的感觉了。他每天机械地执行着命令:饿着它,然后把食物放在德国坦克的车底下。
他不再和狗说话,不再偷偷给它加餐,甚至很少去抚摸它。他的心,好像跟着“闪电”一起死掉了。他看着那些新来的、充满热情的年轻训犬员,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。他想提醒他们,想告诉他们这个计划的愚蠢和残忍,但话到嘴边,又咽了下去。
在绝望的战争中,真相是最无力的东西。
经过“改良”的“狗弹”部队,又被零星地投入了几次战斗。效果依然不理想。虽然它们不再大规模地攻击己方目标,但德军已经完全识破了这种战术。
德国步兵手册上甚至更新了条例:在战场上,优先射杀任何单独冲向坦克的狗。德军机枪手们把猎杀这些“狗弹”当成了一种娱乐。有时候,他们甚至会故意用火力把狗驱赶到开阔地带,然后慢慢地将其射杀。
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“奇招”,彻底沦为了一个悲惨的笑话。
随着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的转折,苏军自身的坦克产量大幅提升,SVT-40半自动步枪、PTRS-41反坦克枪等更有效的单兵武器也开始大规模列装部队。那个荒诞的“反坦克犬”计划,终于被悄无声息地废弃了。
官方的战报上宣称,在整个战争期间,反坦克犬部队“可能”摧毁了多达300辆德军坦克。但所有亲历者都知道,这个数字里包含了多少水分和宣传的成分。对于伊万等底层的士兵来说,这个计划留下的,只有战友无谓的牺牲、被自己人炸毁的坦克,以及那份永远无法释怀的、对最忠诚伙伴的愧疚。
计划解散的那天,伊万负责将他训练的最后一条高加索犬移交给后勤部队。那条狗似乎预感到了分离,不停地用头蹭着他的手。
伊万的手僵在半空中,犹豫了很久,最终还是落在了它的头上,轻轻地抚摸着。这是几个月来,他第一次这样做。
“你自由了。”他低声说,“去当一条真正的狗吧。”
7
战争结束了。伊万活着回到了西伯利亚的家乡。他脱下军装,重新成为了一名牧羊人。
广袤的草原和森林治愈了他身体的疲惫,却无法抚平他内心的伤痕。他放牧着一大群羊,却终生没有再养过一条狗。村里的人都觉得奇怪,这个曾经全区最出色的训犬员,现在却对狗敬而远之。
有时候,村里的孩子们会牵着小狗在他身边跑过,小狗摇着尾巴,想要亲近他。伊万会下意识地后退一步,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。那不是厌恶,而是一种深深的悲伤。
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是他的朋友,有时候会开着轰鸣的拖拉机来找他喝酒。每当那“KTZ”拖拉机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时,伊万的脸色就会变得苍白,拿酒杯的手也会不由自主地颤抖。
朋友察觉到了,关心地问:“伊万,你怎么了?脸色这么难看。”
伊万摇摇头,勉强笑了笑:“没事,老毛病了。”
他从不说起战争中的事,尤其是关于“反坦克犬”计划的一切。那段记忆被他埋在心底最深处,像一颗永远无法取出的弹片,在每个寂静的夜里隐隐作痛。他会梦到“闪电”,梦到它冲出战壕时回头看他的那一眼,梦到那团吞噬一切的黑烟,然后在一身冷汗中惊醒。
几十年后,伊万已经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。一个对二战历史感兴趣的年轻记者找到了他,希望能采访他这位“传奇的反坦克犬部队”的幸存者。
他们坐在伊万简陋的木屋前,喝着热茶。记者兴奋地问起那些官方宣传的“英雄事迹”。
伊万沉默了很久,他的目光越过眼前的草原,望向遥远的天际。夕阳的余晖,将他的白发染成了金色。
“没有什么英雄。”他缓缓开口,声音苍老而平静,“那不是狗的错,也不是它们的战争。”
记者愣住了,准备记录的手停在了半空中。
伊wan转过头,看着这个年轻人,浑浊的眼睛里,映出了多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早晨。
“是我们,在绝望中,把我们最忠诚的朋友,变成了最愚蠢的武器。”
嗨牛配资-嗨牛配资官网-配资知识网站-正规网上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