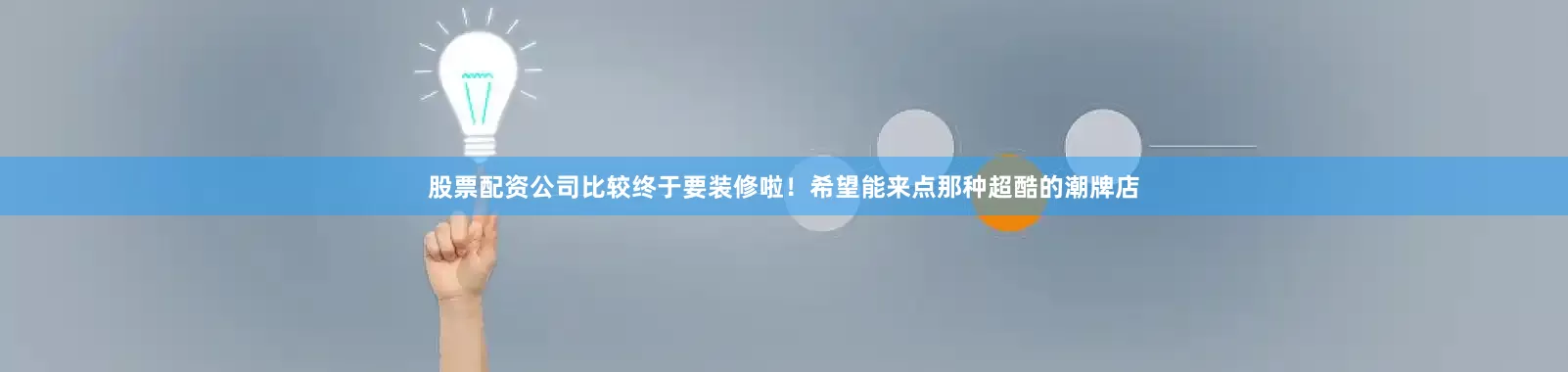“阿曾,你又瘦了。”1953年3月,在中南海怀仁堂侧门,警卫悄声招呼来宾。毛主席推开人群,目光定格在一位身着灰呢中山装的妇女身上,随即故作不悦地皱起眉头:“阿曾,你怎么都不来看我?”场面一静,随后响起轻快的笑声。这一幕,成了第二届全国妇代会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插曲。
能让主席在百忙中冒出一句玩笑话的女人,并不多。曾宪植算一个。她是曾国荃的玄孙女,穿旗袍时婉约,披军装时凌厉,当年在武汉黄埔分校被同学们起了个亲切外号——“黄埔校花”。她却对这个称呼半点不上心,喜欢的还是操场边的泥土味和弹壳声,那些味道提醒她,自己并不是来这里学“体面”的。

时间拨回1923年初夏,长沙城里蝉鸣不断。湖南女子师范学院礼堂里,讲授《世界大势与中国出路》。讲台下,17岁的曾宪植正伏案速记。课后,徐特立拍拍她的肩膀:“女同学也能救国,可别把自己困在闺房。”这句话击中了她。此后,办壁报、拉同学看赛球,她折腾得学校像开了天窗。女孩子穿背心短裤跑动的场景,在当时的长沙并不多见。
父母当然不乐意。曾家小楼内,父亲放低声调:“再闹,家门就别回了。”曾宪植没辩解,她把写满读书计划的薄册往桌上一放,转身离家,直接坐轮船去了武汉。1927年春,她考入黄埔武汉分校女子队,三公里武装越野照跑,翻越壕沟也从不落队。军校男生私底下打趣:“这样漂亮的姑娘,扛枪都不掉漆。”她听见,只当笑料。

北伐打响后,她随军奔向前线,火线救护、传令、抬担架样样干。一次夜渡湘江,她蹚水过河,湿透的棉衣贴在身上,冻得直哆嗦,却依旧稳稳举枪。在那个枪响不断的年代,这样的场景很多,可真正留下姓名的人并不多。她留下了,因为表现出众,被同袍称作“冲锋队里的花木兰”。
也是在黄埔时期,她遇到叶剑英。两人讨论战术图时常常一句话就能接上对方的思路,因此暗生情愫。广州起义失败,两人辗转香港,结成夫妻。可惜革命岁月多风雨,分离成了常态。1930年底,组织安排留苏名额紧张,她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同志,自己留下打地下交通线。小别成为长别,这段婚姻后来无疾而终。
上海冬夜的雨冷得厉害。为了掩护同志撤离,她在南京路被捕。审讯室里灯光刺眼,敌人扬起皮鞭,她却一句口供未吐。同志们几番营救,她才得以脱身。1934年再赴日本求学,不料特务追到东京。被捕那日,她亮出曾国藩后人的身份,日方一听,讶异于这个年轻女子的血统,居然还真给面子,几番审查后把人放了。

1937年夏,她沿海路回国,抗战正酣。她没有犹豫,直奔延安抗大报到。初见毛主席那天,窑洞灯火昏黄。主席翻阅学员名单,嘴里含笑:“名单里这个‘曾’字,我读半天,原来是黄埔阿曾。”她故意学他语气:“主席,我就是那个阿……阿……阿曾。”绵延黄土坡下,众人乐不可支,也让这位出身名门的姑娘迅速融入陕北的简陋环境。
在延安,她参与筹建妇女工作委员会,推广识字班,还给前线战士缝军鞋。有人调侃她绣花针握不稳,她把指尖戳得通红也没放下针线:“能让战士少磨破一双脚,总比我照镜子强。”这句话传开后,不少男兵都来帮她运鞋底原料。延安的夜晚,纺线车吱呀作响,她和姐妹们讨论婚姻观、讨论土地法,那些思想的火花,后来都落进新中国的法典里。

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,她随中央机关进城,旋即参与筹建全国妇联,担任宋庆龄、的秘书。文件堆成山,她照样每周下社区,访贫问苦。一次走访,老厂工递给她一双沾满机油的手套:“干部同志,您穿得干净,别沾脏。”她没接手套,抬手就把机油抹到自己袖口:“怕脏,就别来基层。”一句话,说服对方,也提醒自己。
1953年妇代会期间,主席那句玩笑话掀起哄堂笑声后,两人并肩而坐。主席问:“妇女工作怎样?”她回答:“百废待兴,却也生机勃勃。”主席点头,语调突然严肃:“妇女能顶半边天,可别只是口号。”她随声附和:“所以要真抓实干,要让农村姑娘拿起锄头也能拿起笔。”两人又交谈许久,直到工作人员催促才散。
会后,她分管妇联国际部,对外联络频繁。1955年接待亚非妇女代表团时,一位非洲代表惊讶于她的中文名和流利英语。代表问:“你怎么学会这么多语言?”她笑着说:“打仗逼出来的。”轻描淡写,却藏着半生风刀霜剑。

1960年代,她主动请缨下放农村调研。陕西蓝田的冬土干裂,北风吹得人脸发疼。她挽起裤脚,与妇女们一起担粪、播种。夜里,油灯昏黄,她记清一条条意见:托儿所缺奶粉、公共浴室不够、缝纫机太少。北京来函催她回城,她写信回绝:“情况没摸透,不走。”字迹不潦草,却透着倔劲。
改革开放伊始,她已是白发,却依旧奔波在妇女就业培训现场。有人劝她退休安度晚年,她淡淡一句:“累是累,可想到当年战场,今天这点事算什么?”说完提着包就进工厂,留下年轻干部面面相觑。

2011年冬天,她在北京安静辞世,享年一百零一岁。遗物简单:一枚黄埔校徽、一把缝补过无数次的布挎包、几张褪色的延安合影。有人感慨,黄埔校花到延安十美,再到新中国妇女事业骨干,半个世纪翻山越岭,她失去了不少,但始终保留了三样东西:刚烈骨气,敏锐思考,和那句对自己始终有效的叮咛——“女子也能救国。”
从湘江急渡到怀仁堂问候,历史长卷里她的名字并不闪亮,却总在关键节点留下清晰坐标。阿曾,这个俏皮的称呼背后,是一位女性革命者在风雨七十年的深深足迹。
嗨牛配资-嗨牛配资官网-配资知识网站-正规网上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